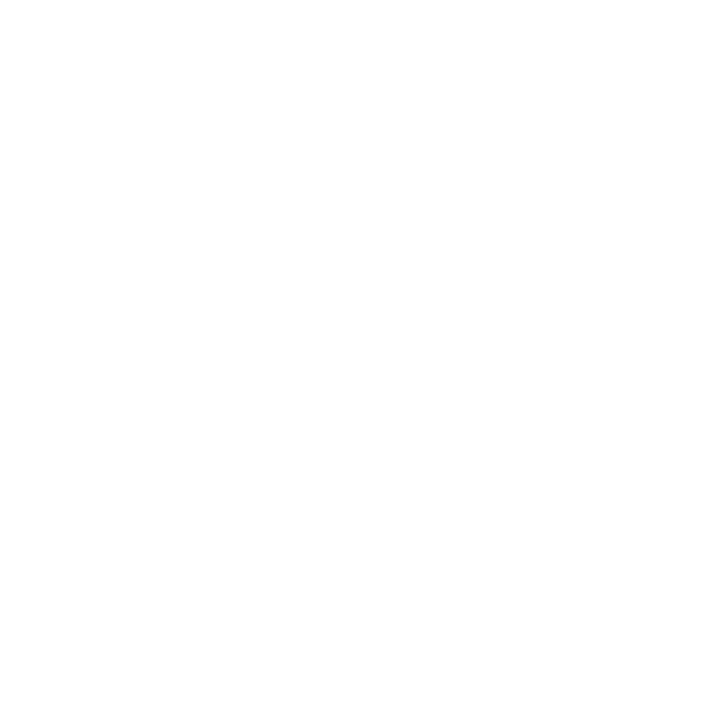北风初起时,总爱在乡野间翻找旧时光的碎片。这时的风尚存着三分温柔,像母亲抚过孩童发梢的手,将零落的银杏叶卷成金色的漩涡,送往那片无垠的蔚蓝。天空蓝得发亮,仿佛被岁月擦拭过的琉璃,连半丝云絮也不肯栖留,只余下几缕若有若无的炊烟,在极高处与风絮语。
收割后的田野裸露出褐色的肌肤,稻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像是大地写下的密码。麻雀们扑棱着翅膀,在空旷的田垄间跳跃,它们尖细的啁啾声里,藏着对散落谷粒的觊觎。偶尔有农人扛着锄头走过,惊起一片雀影,那些金黄的小点便忽地升腾起来,在半空划出凌乱的弧线,又匆匆落回更远处的田埂。这样的场景总让我想起祖母的针线筐,那些散落的谷粒,恰似她缝补岁月时遗落的金线。
暮色四合时,村庄便开始酝酿一场盛大的仪式。炊烟从青瓦白墙间袅袅升起,先是几缕,继而连成一片,在屋顶上织就一张灰白的网。最诱人的是那股独特的烟熏香——客家人用稻谷壳闷米酒的技艺,是岁月传承的秘方。谷壳在灶膛里噼啪作响,暗红的火光舔舐着陶瓮的腹部,将米酒的醇香与谷壳的焦香揉作一团。这香气不似花香那般清冽,倒像是陈年的木箱被突然打开,涌出的全是时光沉淀的味道。
隔壁阿婆家的厨房里,糯米熏鸡的香气正与米酒香缠绵。糯米裹着鸡肉,在慢火中渐渐酥软,鸡油渗入米粒,米香又渗入鸡肉,彼此渗透,彼此成全。我常想,这大概就是客家女人最朴素的哲学——不争不抢,却能在交融中成就彼此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年关,母亲总会做这道菜。她系着靛蓝的围裙,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,被蒸汽氤氲得有些模糊。而今,阿婆的厨房里,同样的香气升起,却再也寻不见母亲围裙上的补丁。
村口的老槐树下,几个孩童正围着卖糖画的老人。老人手中的铜勺游走如龙,糖汁在青石板上流淌成蝴蝶、鲤鱼、莲花。孩子们踮着脚,眼睛瞪得溜圆,喉咙里吞咽着口水。这场景与三十年前并无二致,只是当年那个攥着五分钱的孩子,如今已两鬓斑白。糖画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,像是凝固的时光,甜得让人心颤。
夜幕降临时,星星开始在天空闪烁。老人们端着搪瓷缸,聚在祠堂前的石凳上聊天。他们的话题从今年的收成,转到远行的儿孙,又落到村东头那口古井的水质。言语间,岁月被揉成一个个温软的故事,飘散在寒夜里。我常想,这些故事大概就是客家人的根,一代代传下去,便成了血脉里的印记。
远处传来鞭炮的脆响,惊得几只夜鸟扑棱棱飞起。这零星的鞭炮声,是新年将至的信使。在客家人的年历里,新年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日子,而是一段渐次浓郁的时光。从第一缕米酒香飘起,到最后一挂鞭炮余音散尽,这中间所有的等待与期盼,所有的忙碌与欢喜,都是岁月赐予的礼物。
北风依旧在吹,卷着几片残叶掠过屋檐。我站在院子里,深吸一口混合着米酒香与熏鸡香的空气,忽然明白,所谓新年,不过是时光给我们的一个借口——让我们在忙碌中停下脚步,回首往事,展望未来,然后在烟火气里,重新找回生活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