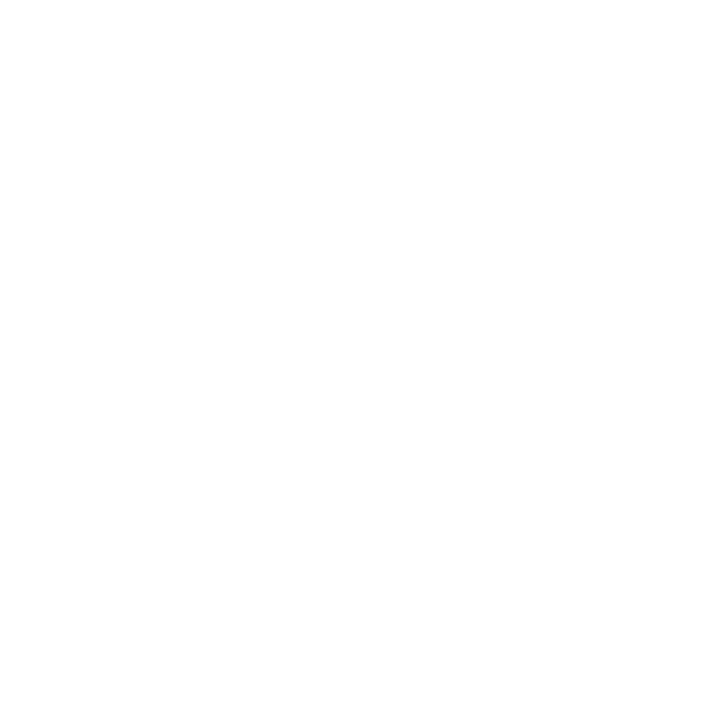在这空气中弥漫着桂花香气的深秋时节,有幸参加户外采风活动,得以亲临赭亭山,一睹它的真面目。赭亭山坐落于江西省横峰县的北面,前面是广袤的湖泊群,连绵不断的湖泊群山水相连,风景旖旎,颇有横峰版千岛湖的气势。
有些山的重量,从不在海拔的数字里。赭亭山的红,是岩层的底色,更是岁月浸不透的记忆——每一道石阶的凹痕、每一寸树皮的弹痕、每一缕裹着信江水汽的风,都在悄悄说:那些曾绕山而行的人,从未走远。
赭亭山不高,赭红色的岩层却像浸了浓墨似的,连晨露落在上面,都晕不开那沉厚的红。我攥着铁链往上攀,冰凉的铁屑蹭过掌心,鞋尖每一次磕在石阶上,都能听见“咚”的轻响——这石阶被岁月磨得边缘发圆,却仍留着细碎的凹痕,老人说,那是当年红军战士扛着弹药、踩着露水绕山去打水时,鞋底反复蹭出的浅痕。风从山谷里钻出来,裹着松针的清苦往衣领里灌,惊得枝头几只山雀扑棱棱飞起,翅膀扫过脸颊时,带着一丝羽毛的软,恍惚间竟像触到了记忆里战士们粗布军装的质感。
“慢些走,这阶滑。”半山腰的拐角处,忽然传来低柔的声音。我抬头,见一位老奶奶正蹲在老松树下,手里攥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帕子,正一点点擦着树干上的弹痕。那弹痕深约指节,边缘的树皮早已结痂,她却擦得极轻,像在拂去亲人肩头的尘土,帕子蹭过木刺的“沙沙”声,在山间静得能听清。“当年他们就靠在这树后躲子弹,”她没回头,声音裹着风飘过来,“我爹说,夜里常听见松树‘呜呜’响,像在替没回家的人哭。”竹篮放在脚边,里面躺着几束野菊,花瓣上沾着的草屑还没抖掉,旁边军绿色的水壶斜斜靠着,壶嘴沾着的泥点还带着潮气,一看就是刚绕山走了远路的样子——两里外的信江,想来她就是顺着战士们当年的小路过去的。
我挨着她蹲下来,指尖轻轻碰了碰石阶,晨露的凉顺着指尖往骨缝里钻,却能清晰摸到石板上深浅不一的纹路。“这是红黑硝炸的印子。”老奶奶忽然指着不远处一块石板,上面的赭红深得发暗,边缘还留着焦黑的痕迹,“血渗进去,雨水冲了这么多年,还是红的。”她起身时扶了扶腰,往山顶的方向望了望,脚步慢却稳,每走几步就停下来,用帕子擦一擦石阶上的泥,像在为远行的人清理归途。我跟在后面,听着鞋底蹭过石板的咯吱声,忽然觉得这路不是在往上走,是在往岁月里走——每一步踩过的,都是战士们当年扛着水壶、攥着枪托踏过的地方。
快到山顶时,风忽然变了味,混着一丝水的清润。抬头望去,能看见绕山的小路像条淡褐色的丝带,从山根处蜿蜒开去,尽头隐在绿树后面,那便是信江的方向了。“当年他们绕着山去打水,来回要走小半天,”老奶奶的声音有些发颤,“裤脚卷到膝盖,腿上划满了草口子,却总说信江的水甜,能润嗓子。”说话间,我们已站上山顶。她从篮里拿出两个白瓷碗,拧开水壶盖,信江水“哗哗”流出来,带着些微的凉意,落在碗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“尝尝?”她递来一碗,我接过来,指尖碰到碗沿的温度,竟像触到了当年战士们捧着水壶的手。
风又起了,裹着信江的水汽扑在脸上,带着水特有的软。往山下望,绕山的小路在阳光下泛着微光,两里外的信江虽看不见,却能想象出它绕着山、静静流淌的样子。老奶奶把野菊摆在那块最深红的石板旁,瓷碗轻轻放在花前,“当年你们没喝够的水,今天多喝点。”她站了会儿,伸手摸了摸石板,指腹在上面轻轻打了个圈,像在与老朋友道别。我忽然懂了,这山的红不是颜色,是能摸得着的温度;这绕山的路不是痕迹,是能走得到的记忆;这两里外的信江不是远方,是能尝得到的思念——没有碑石,可每一块石阶、每一寸树皮、每一缕风,都在替没回家的人,守着这片土地。
下山时,风里的松涛声混着远处隐约的水声,像有人在耳边轻轻说:“别忘啊,别忘这山为何红,别忘有人曾绕着山、蹚着河,把命留在了这里。”我攥紧了手心,那里还留着铁链的凉、石阶的润,还有信江水的甜——这些触感落在心里,比任何文字都更能让人记得:有些岁月,从来不是听说,是能摸着、能尝着、能走着的。
后记:
下山时回望,夕阳正给赭亭山的岩层镀上一层暖光,那抹红比清晨更显厚重。老奶奶说,她每个月都会来,带一束野菊,打一壶信江水——不是为了纪念,是怕那些藏在石阶、树皮里的故事,没人再听。
其实不用怕。当指尖触到石阶的凉,当舌尖尝到江水的甜,当风里飘来松针的苦,那些故事就会从岁月里走出来,轻轻落在心里。原来最好的铭记从不是刻在碑上,而是藏在“记得”里——记得这山为何红,记得那些曾为这片土地跋涉的人,便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