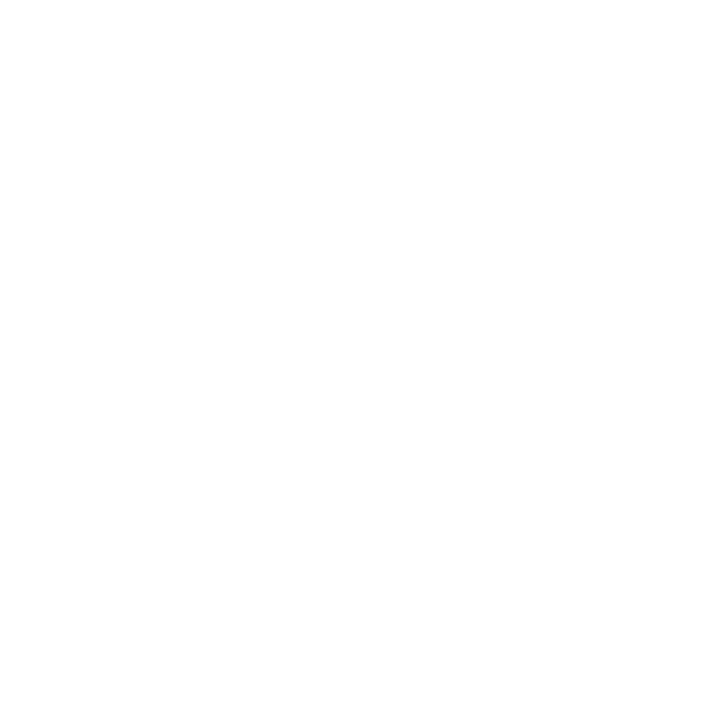父亲弓腰拨开麦浪时,军绿胶鞋正陷在苦菜丛生的田埂里。麦芒如银针,在他古铜色的小腿上刺出星图——这些细密红痕与粮仓土墙的划痕相映,都是丈量年景的古老密码。糜草枯黄的碎屑黏在裤脚,像某种关于消亡的注脚。
晒场边的母亲咬断麻线,青丝里麦芒般的银发掠过蚕茧状的耳坠。三十年前她掐断茧尖的指尖,此刻正摩挲着新补的麻袋,袋口留着去年祭车神的朱砂印。"芒种刀口,小满籽口。"她将稗子抛向啄食的麻雀,篾匾里青黄参半的麦粒突然簌簌颤动——原是父亲在渠坝跺脚,震落裤管的紫云英残瓣。
铜烟锅斜插麦丛,露水顺雕花烟嘴滴成弧线。"灌浆声比九八年还欢。"父亲抹了把额角的盐晶,那是南风携来的海雾凝成的。暮色漫过打谷场时,他们化作两株会移动的草垛,母亲突然举起株麦穗,穗尖尚未褪尽的青涩里,籽粒已显出玉质的通透。
月光涨满麦垄的刹那,山歌调惊醒了沉睡的轧车。父亲往水车轴榫里楔入新木的声响,母亲摇动纺车的嗡鸣,与千里外收割机的轰鸣在潮湿的夜色里发酵。我忽然看清粮仓土墙的划痕深处,还嵌着幼年用桑葚汁涂写的"小满"二字。
南风掠过待修的轧车,将苦菜的苦香、糜草的朽味与新麦的乳香糅成团。父母霜白的鬓角沾着夜露,那是比春蚕尿更清亮的液体,正在月光里酝酿某种微妙的平衡——就像此刻灌浆的麦粒,将满未满的丰盈中,饱含着对圆满的永恒警惕。